网上有关“致一百年以后的你怎么样”话题很是火热,小编也是针对致一百年以后的你怎么样寻找了一些与之相关的一些信息进行分析,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希望能够帮助到您。
“我的诗啊写得那样地早......” 茨维塔耶娃在 1931 年回答某一家期刊问答表中“关于 您的创作您有何想法?”一项时曾引用过这首诗的最后一行。 1933 年 4 月在回复尤·伊瓦斯科的信时曾写道:“琼浆玉 液”写于 1913 年。这是我的写作的(以及个人的)生涯的公 式——前景。一切我都知道——生来就知道。” 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曾为这首诗谱曲。 “我这会儿伏卧在床上......” 这首诗是献给 M. C. 费尔德施泰因(1885-1948)的,他 后来成了茨维塔耶娃的大姑子维·埃夫伦的丈夫。 给外祖母 这首诗是献给诗人的外祖母玛·卢·别尔纳茨卡娅 (1841-1869)的,她的像当年悬挂在茨维塔耶夫家中。1933 年诗人发现,那张像并非是她的外祖母,而是外祖母的母亲。 “我喜欢——您不是为我而害相思......” 这首诗是献给马夫里基·明茨(1886-1917)的,他后来 成为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妹妹阿纳斯塔西娅·茨维塔耶 娃的丈夫。这首诗由苏联作曲家 M·塔里韦尔季耶夫谱曲, 成为一首广泛流传的歌曲。 “任谁也没有夺走什么东西......” 这首诗是写给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1891—1938) 的,后者于 1916 年来到了莫斯科。茨维塔耶娃对曼德尔施塔姆的创作评价很高,认为他的诗富有魔力、魅力,虽然有些 思想混乱,但仍肯定他的诗有“杰尔查文的手法”的痕迹。曼 德尔施塔姆在 1916 年也曾写过数首诗献给茨维塔耶娃。 “哪里来的这般柔情似水?......” 这首诗也是献给曼德尔施塔姆的,肖斯塔科维奇曾为之 谱曲(第 143 号组曲)。 莫斯科吟 《莫斯科吟》这组诗共 9 首,是在 1915-1916 年冬彼得 堡之行的灵感之下创作的。茨维塔耶娃希望见到阿赫马托 娃,后者当时却不在。在有叶赛宁、库兹明、曼德尔施塔姆出 席的文学晚会上,茨维塔耶娃“代表莫斯科”朗诵了自己少女 时代的诗作,对此,她在许多年后回忆时写道:“我朗诵着 ——就仿佛阿赫马托娃真的在这房间里,只有阿赫马托娃一 个人......如果说此刻我想将自己比作莫斯科——再好不过 了,那么不是为了战胜彼得堡,而是为了把莫斯科献给彼得 堡......我从彼得堡归来之后写就的关于莫斯科的诗篇,我是 要归功于阿赫马托娃的;我对她的爱以及我的祝愿,要求献 给她比爱更为永恒的东西。”这里选译 4 首。 1.“夜晚打从钟楼经过......” 这首诗是献给奥·曼德尔施塔姆的。 4.“一串串花楸果......” 1934 年茨维塔耶娃关于这首诗写道:“这是我最喜爱的, 我自己本人的诗作之一。” 失眠在茨维塔耶娃早期的诗作中,时常表现失眠的主题,《失眠》这组诗共 11 首,其中第 3-第 10 首是受到尼·普卢采 尔-萨尔纳(1881-1945)启发创作的,后者从 1915 年春天起便成了茨维塔耶娃的至交,并曾在她生活极端困难时刻给 予她多方面照顾。茨维塔耶娃在 1941 年 5 月 3 日曾在组诗 《致阿赫马托娃》的一首诗下面写过这样的话:“所有这些诗, 从这里起到本诗集〔《里程集》〕结尾,以及后来的许多诗,都 是写给尼科季姆·普卢采尔-萨尔纳的,提到他,过了一辈 子以后,我可以说,他很会爱我,会爱我这个难以交往的东 西。”这里选译 4 首。 致阿赫马托娃 组诗《致阿赫马托娃》共 13 首,其中第 10 首未完成。茨 维塔耶娃于 1912 年开始接触阿赫马托娃的创作,1915 年写 了一首献给后者的诗。1916 年这组诗是茨维塔耶娃 1915- 1916 年冬季彼得堡之行时得到的灵感而写的(参见《莫斯科 吟》题解)。茨维塔耶娃在很长的时期里一直保持着对阿赫马 托娃的深情,这一点从她 1921 年 4 月写给阿赫马托娃的信 里便可说明:“啊,我多么爱您,我多么为您而感到高兴,我多 么为您而痛苦,又多么因为您而感到崇高!”1926 年从国外, 茨维塔耶娃依然表示了对阿赫马托娃的爱。阿赫马托娃怀 着深情厚意接受了这一致意,并且把自己的诗集签赠给茨维 塔耶娃。茨维塔耶娃原本对阿赫马托娃的创作评价很高,但 后来,在 1940 年读了阿赫马托娃的全部作品以后,却改变了 看法。她们两人的唯一一次会见是于 1941 年 8 月 7-8 日 在莫斯科举行的,但却没有得到互相理解。 阿赫马托娃曾把组诗之一的首句“啊,哀歌的缪斯,缪斯 中最美的女神!......”作为她的诗作《科马罗沃小村素描》 (1916)的题词。这里选译了 1 首。 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曾为此诗谱曲(作品 143 号组曲)。 “苍白的太阳和低沉的、低沉的乌云......” 这首诗写于茨维塔耶娃的家乡亚历山德罗夫,当时正是1916 年士兵们上前线打仗,在她居住的房子前边,庭园的那 边有一块场地,士兵们正在练习射击。诗人在一篇文章里谈 到这首诗时写道:“我们向士兵们挥动头巾,而士兵们向我们 挥舞着帽子,当最后一节车厢早已从视线中消失的时候,士 兵们唱歌的号叫声连同火车头的浓烟迎面而来。” 唐璜唐璜是中世纪西班牙传说中的青年贵族,欧洲许多文学 作品中的主人公。最初以否定宗教的禁欲道德的形象出现, 后来发展为极端个人主义者的典型。他被视为仗着自己财 势,以结婚为手段,到处玩弄女性的花花公子。茨维塔耶娃 1925 年在给一位友人写信时曾说:“......即使唐璜一往情深, 他怎能爱所有的人?这个‘所有的人’是不是逢场作戏的老一 套的结果?简而言之:爱所有的人——悲剧式地,怎么可能? 殊不知,唐璜是可笑的......也许这个所有的人的悲剧性,爱 所有的人的悲剧,乃是女人的特权(我深有体验)?” 组诗共 6 首,选译 3 首。 斯坚卡·拉辛 斯杰潘(爱称斯坚卡)·拉辛(约 1630-1671)是俄国农 民起义的首领,后被沙皇处死。茨维塔耶娃所感兴趣的,不 是历史上的拉辛,而是他在著名的民歌中的形象。茨维塔耶 娃在谈到与拉辛式的红军战士会见时写道:“......我的拉辛 是(民歌中的)浅色头发的男子,——一头浅棕红毛发的男 子......再说这个词本身:斯杰潘!干草,禾秸,草原。难道有 黑色的斯杰潘吗?而拉——辛!曙光,春汛,——打击,拉辛!” 诗人在“斯杰潘·拉辛”姓名之后列举的词,不仅读音与前者 相近,而且还有相近的意思。 组诗共 3 首。 “我是你笔下的一张纸......” 茨维塔耶娃在 1939 年手稿附记中说:“这是集子里最优 秀的诗作之一”在《一首献诗的经过》一文中引用这首诗时曾 写道:“当年,1918 年,我是否意识到,在把自己比作最简单的 东西(黑土和白纸)的同时,我指的是最伟大的东西:矿藏(黑土)和白纸的万能?作为一个虔诚的热爱者,我为什么把自己 只比作一切?我是否意识到了——他是否也意识到了?” 1918—1931 年。做过一次修正:“这样说只能是对上帝。 须知,这是一种祈祷!对人,是不用祈祷的。十三年前,这一 点我还——不,知道!——坚决不想知道。而且——不可更 改地——我的所有的这类诗,整个是献给上帝的。” “宛若左右两只膀臂......” 据1939 年茨维塔耶娃笔记记载,她认为这是她早年优 秀诗作之一。 “像星星,像玫瑰,生长出诗......” 这首诗的第 5 和第 6 两句是由茨维塔耶娃的小女儿阿 利娅记载的一段事引起的:“那是温馨的一天,我同玛丽娜去 散步......顶上是一座大教堂......我突然发现,在我脚下生长 着三叶草。在小台阶前那里平整地铺着古老的石头。每块 石头都由三叶草镶着深色的框框......我......开始......寻觅 四叶草......我突然找到了它......我跑到玛丽娜跟前,把我的 所获献给了她......她对我表示感谢并把它夹在笔记本里变 干。”阿·埃夫伦在她的回忆录中引用这首诗时写道:诗中出 现了“从前在优美的庞然大物‘菲利小镇波科罗夫’的山脚下 寻找到的那株......象征幸福的、四片叶子的三叶草的幼芽”。 丑角《丑角》这组诗是由 25 首构成的,先后在不同的题名下发表,最后集到一起,因此,诗的次序并不固定。这组诗是茨 维塔耶娃与艺术剧院(后为瓦赫坦戈夫剧院)创作室年轻演 员们的友谊的折射。这段期间虽然不太久,但她的创作是颇 有成效的:为剧院创作了许多部浪漫主义的诗剧,组诗《丑角》、《献给索涅奇卡的诗》(1919),以及后来写的散文《索涅 奇卡的故事》(1937)等。 《丑角》是献给演员和导演尤·亚·扎瓦茨基(1894- 1977)的。茨维塔耶娃认为自己与扎瓦茨基的关系就像“中了 魔法”。但是这种“中了魔法”却是与理解的清醒并存的。茨 维塔耶娃在当时的笔记中对扎瓦茨基有这样的记载:“他那 深沉的天真无邪的全部的美和全部的可怕。......那名利的 天真无邪,那自尊的天真无邪,那健忘的天真无邪,那束手无 策的天真无邪......总之,作为一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作为生 物却是完美无缺的......对于我来说从他的所有的诱惑中我 可以分出来三点:软弱的诱惑,冷漠的诱惑,陌生人的诱 惑。”由于评价的清醒,诗人便对自己的主人公的态度和对自 己的“中了魔法”的态度报以揶揄。茨维塔耶娃认为扎瓦茨 基“从来就不是我的朋友”,因而整组诗都带有轻蔑的嘲讽。 这里选译 2 首。 “我告别了英格兰浓雾弥漫的海岸......” 献词和诗的头一句引自俄国诗人康·巴丘什科夫 (1787-1855)的悲歌《友人的影子》(1814),诗是为纪念诗人 的一位在莱比锡城下“人民的战斗”中牺牲的友人而创作的。 茨维塔耶娃似乎是将巴丘什科夫的悲歌加以“改写”,纪念为 希腊自由而献身的拜伦之死的。 致一百年以后的你 茨维塔耶娃在 1919 年笔记中曾记载:“昨天一整天都在 思考一百年后这件事,于是为此写了几行诗。这些诗行已经写就——诗将发表。”1924 年在一封信里又说:“而且——主 要的——我深知一百年以后人们将会多么爱我!(阅读—— 什么!)”这首诗还有另一种版本,这里译的是诗人 1940 年的 定稿。 “我在青石板上挥毫......” 这首诗是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献给丈夫谢·埃即谢尔 盖·埃夫伦(1893-1941)的。他早年参加了白军,溃败后流 亡捷克;1922 年茨维塔耶娃携幼女阿利娅离开苏联去投奔丈 夫。后来埃夫伦在国外参加了苏联的一些情报活动并于 1937 年回国,阿利娅已先期归国,1939 年茨维塔耶娃携子穆尔亦 返回苏联。但不久阿利娅与埃夫伦先后被捕,杳无音信。1940 年诗人在编选诗集时曾将“我在青石板上挥毫......”一诗作 为开卷篇收入其中,在个人家庭的悲惨的遭遇下,诗人以这 种隐晦的方式将此选集献给了丈夫,这充分表现了她的良苦 用心和难言之隐。据研究者推断,从技巧的娴熟,风格的洗 练,语言的深邃上来讲,此诗当属 1940 年之作。本诗的第二 节,作者曾有 40 余种不同草稿,可谓精雕细镂。 两首歌 《两首歌》是诗人于 1920 年为诗剧《门生》而写的,尚有 其他数首,剧本已失传。 眼睛这首诗最初次发表时是献给先为象征派后转向阿克梅 派的诗人米·库兹明(1875-1936)的,1916 年 1 月茨维塔耶 娃在彼得堡见到过他一次。1921 年茨维塔耶娃见到库兹明 的诗集《不是这里的晚上》以后,曾绐库兹明寄去一信并附此 诗。库兹明 1921 午 7 月 8 日日记中记有此事。这首诗是对 那次会面的回忆。茨维塔耶娃在评论文章《不是这里的晚上》中记有这次会面:“这不,从大厅的另一端,遥远的——就 像用望远镜倒过来看似的;一双硕大的——像从望远镜的正 面看似的——充满了所反映的望远镜的整个镜头——眼睛。 在彼得堡的上空呼啸着暴风雪,在暴风雪中像两颗行星呆滞 地停立着两只眼腈......停立着?不,走过来......从大厅的另 一端——像两颗行星呆滞地——向我走过来两只眼睛。眼睛 就在这里。站立在我的面前——库兹明。” 青春茨维塔耶娃在创作“我的青春啊,我的视同陌路的......” 这首诗时,曾有记载:“一切都早于大家:十三岁即热衷于革 命,十四岁以及现在模仿巴尔蒙特,二十九岁......与青春诀 别了。” 黎明时分...... 这首诗是描写史诗《伊戈尔远征记》的形象的。 尘世的特征 这组诗共 8 首,选译 1 首。这首诗表现的是茨维塔耶 娃作品中多次出现的关于两种爱的思想——以维纳斯、夏娃、荷马的海伦为化身的尘世的爱和以普绪刻为化身的精神 的爱。她在 1923 年的一封信里写道:“......肉体(我们个人 兴趣的癖好)是极残忍的。普绪刻(看不见的)之所以为我们 永恒地爱,是因为爱我们心里缺席的东西的——只有灵魂! 我们以普绪刻来爱普绪刻,我们爱斯巴达王的海伦......却差 不多是用手——我们的眼睛和手从不想让她的眼睛和手丝 毫地偏离开美的理念的线条。普绪刻不会受到审判——清 楚吧?海伦却不断地站在审判官面前。” 电报线 这组诗共 10 首,是献给苏联著名诗人鲍里斯·帕斯捷 尔纳克(1890-1960)的。帕斯捷尔纳克最初于 1921 年由于 对茨维塔耶娃的诗集《里程集》的强烈感受而开始与她通信。 他对她的创作终生表示赞赏,并曾写过数首诗献给她。此外, 还在自传体散文《人与事》中回忆过她。茨维塔耶娃于 1922 年出国后不久,多年一直与帕斯捷尔纳克保持着通信联系。 有人认为他们的这种炽热的友谊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爱情”。 茨维塔耶娃认为帕斯捷尔纳克是一位精神上与她最接近的 诗人,是志同道合者,是“一年五季、第六感觉和四维空间的 弟兄”。她又说:“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对我来说是一种最 神圣的东西,这就是我的整个希望,时而是地平线上的天空, 时而是不存在的东西,时而是将会出现的东西。”茨维塔耶娃 致帕斯捷尔纳克的书简有百余封,据说,战争期间,帕斯捷尔 纳克由于十分珍视这些书简曾委托给一位友人保存,而这位 友人也因为十分珍视,以至于每遇到敌人轰炸便带在身边, 不幸最后竟然遗失了。现在只有少数几封保存下来,但在茨 维塔耶娃的笔记本中存有副本,保存在创作档案中,根据茨 维塔耶娃的女儿阿·埃夫伦的遗嘱,待到 2000 年才能启封。 组诗《电报线》可说是在他们两人之间书信往来的灵感 之下创作的,也可说是以通信方式为帕斯捷尔纳克送行。茨 维塔耶娃得知帕斯捷尔纳克来德国访问后拟于 1923 年 3 月 18 日由柏林回国,因为她住在捷克,便于 3 月 9 日给他写信 说:“......这实在是荒谬绝伦——您的启程,是从柏林站台 吗,是从我的波希米亚山上呢,我 18 日一整天(因为不知启 程时间)都将站在这座山上为您送行——只要是精神支持得 住。我不打算去〔柏林〕,因为已经晚了,因为我是无能为力 的......因为这是我们的命运——损失。”接下去是:“这并非 夸夸其谈,这是难以抑制的感情——已经不顾分寸的概念的 感情!——而且我所说的还不及实际。现在照直说吧: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因此我很痛苦。在自己的高处的什么地 方——是寒冰(解脱!),而在深处,在内心——却是痛 苦......” 组诗开首的题词引自德国诗人荷尔德林(1770-1843) 的书信体小说《许佩里翁,或希腊的隐士》(1797-1799),引 文略有出入,——是“生活的浪涛”。 1.“专横的乡间!......” 茨维塔耶娃对约定俗成的尺度和标准一向持否定态度, 这种否定的态度从而转化成对诗律的反动——这首诗中便 蕴含着她的诗歌创作的模式:“这是我的心儿迸发的韵 律——就好像那带有磁性的火星。” 2.“我不是女魔法师!顿河远方的白书......” 这首诗原稿中有一个注,后来写进了给帕斯捷尔纳克的 信里:“这些诗是一些脚印,我沿着这些脚印正在走进您的灵 魂。可是您的灵魂却远远地躲开,以至于非常烦恼的我,正 在赶上去,在跳跃,盲目地,企图侥幸,可是后来却茫然若失 地期待着——它是否会到那里?” 诗中“白书”一词是针对“魔书”而言的,因为俄文“魔书” 字面上的意思是“黑书”,“女魔法师”一词便是由这个词根构 成的。 4.“当我那心爱的弟兄......” 茨维塔耶娃在那篇描写她在艺术剧院创作室时的女友、 女演员索涅奇卡·戈利戴(1896-1935)的散文《索涅奇卡的 故事》中说:“不管怎么说,我还是从她(索涅奇卡)那里偷得 了一首小诗,因为她没有写过诗,生平没有写过一行诗,—— 尽管我非常的、无比的诚实,但是我,不错,还是偷了。这是 我一生中唯一一次剽窃。有一次她对我讲起她受过的一次 委屈时说:‘啊,玛丽娜!我当时的泪珠儿是那样的大——比 眼睛还要大!’‘你要当心,索涅奇卡,我将来会把你这句话偷 入诗中的,因为这句话简直太美了——那么精确......’这不, 三年之后(也许,一天天的,谁又会知道呢)的一首诗:‘当我 那心爱的弟兄......’,而那太平洋上空的星星却在我写索涅 奇卡的 Lacanau-Océan 小镇上空燃烧着,昨夜一点钟,我望 着这些星星,一下子想起这些行诗——相反地:太平洋上空 的星星比眼睛还要大!终于完满了。这些行诗写成以后寄给 了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但是诗的作者和呈献者却是索涅 奇卡。” 布拉格骑士 这首诗写的是捷克人民传奇英雄布伦茨维克骑士的雕 像,它耸立在伏尔塔瓦沿岸布拉格查理大桥附近。根据中世 纪的传说,布伦茨维克即指国王普舍美斯二世,他曾为巩固 捷克王国做出很大贡献。在布伦茨维克统治的第三年,他去 漫游世界,弘扬祖国的语言并寻求狮子的徽记。他经历了冒 险,死里逃生,拯救了狮子的性命;狮子成了他的朋友并且帮 助他建立了丰功伟绩。有一次,他来到了一个岛上的城堡, 在这里他发现了一支宝剑,用它消灭了敌人。之后他回到了 祖国,统治了四十年;他死后,狮子也死在了他的墓地。传说 布伦茨维克的宝剑砌在了他的雕像所在的查理大桥桥墩下。 捷克的国徽的起源便与布伦茨维克的名字联在一起,至今国 徽上仍然有狮子的形象。 茨维塔耶娃认为“布拉格骑士”的面孔与她相像,多年来 她对他一直念念不忘,对于她来说,他就是布拉格的“中心”, 心脏。20 年代,在法国侨居时,她曾写信给她的捷克女友捷 斯科娃,请她寄来一张“他的像,大一些,清楚一些,比如版 画......如果我有保护天使,那么就要长着他那副面孔,有着 他的狮子和他的宝剑”。1938-1939 年,茨维塔耶娃在创作 《致捷克的诗章》时,曾打算写一部大型作品,描绘布伦茨维 克骑士。 两个原稿中曾有献词:“给我的一年五季、第六感觉和四维空 间的弟兄——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在题名 《两个》和《一对》上曾经有过犹豫,后来定为前者。组诗共 3 首,选译 2 首。 忌妒的尝试 这首诗,看来最初是献给康·罗泽维奇(1895-1988) 的,但文学家马·斯洛宁(1894-1976)在回忆录中肯定说, 此诗是献给他的。 爱情在1924 年 9 月末或 10 月初的稿本中记载:“比较:频繁 得有如母亲经常呼唤亲生的孩子的名字。”本诗中最后三行 即源于此。 “鬓角已经银灰......” 茨维塔耶娃在 1926 年 5 月 26 日致帕斯捷尔纳克的信 里说,“......我有几行诗献给你......差一点没写完,是对你的 呼唤,在我心里,也是在我心里对我的。......因为有几处还 没有填上,整首诗不能寄给你。若是想写——这首诗就会写 完的,这一首,还有别的。” “我向俄罗斯的黑麦致以问候......” 这首诗是献给鲍·帕斯捷尔纳克的。在诗人 1925 年 3 月 20-22 日的草稿本中记载:“鲍·帕,我们何时能够见面? 我们能够见面吗?把手伸给我吧——但要待到来世,在这里 呀——我的双手腾不出空。” “赞美啊,静一静!......” 这首诗写于法国。1925 年 11 月 1 日由捷克迁居法国 后,只是第一年冬季茨维塔耶娃全家四口寄居于俄国友人 家,后来住在巴黎郊区,常年处于极端贫困中。在法国生活 的十四年期间,她从未对法国人发生好感,得不到他们以诚 相待。当然同俄国人相处也并不见得好些。 这首诗写作期间,茨维塔耶娃与丈夫和两个孩子挤在 一间屋子里,总是处于干扰之中,找不到一个角落从事创 作。她在 1925 年写给捷克女友捷斯科娃的信里曾描述过这 种处境:“我的日子过得很糟糕,全家四口人挤在一间屋子 里,我根本无法写作。我痛苦地思忖,一个最平庸的散文作 家,甚至连写的什么都没有重读一遍,却能有一张写字台和 两小时清静。可是我却办不到,连一分钟都没有:总是处于 人们包围之中,处于谈话之中,不断地丢下笔记本。” 〈悼念谢尔盖·叶赛宁〉 这是茨维塔耶娃原拟写的长诗的几行。诗人于 1932 年以“诗人与时代”为题曾写道:‘叶赛宁死了,因为他把不是 自己的,别人的需求(时代对社会的)当作了自己的——(时 代对诗人的),把需求中的一项当作了整个的需求。叶赛宁 死了,因为他让别人认识了自己而忘了他自己便是引导—— 最直接的引导!......政治的需求对于诗人来讲不是时代的 需求,时代是不用通过中间人提出需求的。不是时代的需 求,而是当务之急的需求。我们因叶赛宁之死对昨日的当 务之急也负有责任。叶赛宁死了,因为他忘记了自己便是 这样的时代的中间人、代言人、领路人——至少他在某个时 候也同那些为了时代和以时代的名义而把自己扼杀和毁灭 了的那些人一样。” 诗人与沙皇 《诗人与沙皇》是组诗《致普希金的诗》中的两首,组诗 共 7 首。茨维塔耶娃从童年时代起,一生都崇拜普希金的 天才。1913 年她写了献给他的第一首诗。1936 年茨维塔耶 娃曾将普希金的 18 首诗译成法文。为纪念诗人逝世一百周 年,她曾将组诗《致普希金的诗》寄给《当代纪事》杂志。茨 维塔耶娃 1937 年 1 月 26 日在写给捷斯科娃的信里说:“《致 普希金的诗》,我压根儿没想除我以外有谁敢于阅读。这些 诗非常尖锐,非常自由,与规范化的普希金没有任何共同之 处,而且总是与规范相反的。危险的诗作......它们内在是 革命的......内在是叛逆的,每一行都是挑战......它们是我 当时和现在作为诗人一个人对伪善的挑战......它们是 1931 年夏天在默登写成的——我当时正在阅读晓戈列夫(1877- 1931,苏联文艺学家)的《普希金的决斗和死亡》——由于愤 怒而感到窒息。”除诗作以外,茨维塔耶娃还创作有散文《我 的普希金》(1937)和《普希金与普加乔夫》(1937)。 1.“沙皇们的彼岸的大厅......” 关于这首诗茨维塔耶娃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它是“一 个诗人为诗人复仇。因为如果尼古拉一世不把普希金控制 在他的身边——若是能准他出国——允许他到世界各 地——他或许不会为丹台士杀害。内部的凶手便是他”。“彼 岸的大厅”系指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内环绕亚历山大二世纪 念像的陈列馆,天顶装饰着亚历山大二世列祖列宗的肖像, 用威尼斯的马赛克镶嵌而成。在他们之中,也有亚历山大 二世的父王尼古拉一世。 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曾为这首诗以及“不,当我们 为宗师下葬的时候......”两首诗谱曲。 接骨木 茨维塔耶娃在 1931 年给捷斯科娃信中谈到这首诗的写 作时说:“我在写诗——抒情性的——......现在写的是:接骨 木(你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树吗?全是很小很小的有毒的红色 果实,长在栅栏旁边)。” 给儿子的诗 组诗共 3 首。玛丽娜·茨维塔耶娃之子格奥尔吉(穆尔)· 谢尔盖耶维奇·埃夫伦于 1925 年 2 月 1 日出生于捷克斯洛 伐克。他少年时代便极力想回苏联,终于在 1939 年 6 月同 母亲一起返回。茨维塔耶娃对儿子百般宠爱,为了他才不 得不疏散到后方。据 1941 年 10 月 6 日格奥尔吉在诗人克 鲁乔内赫的纪念册中记述:“1941 年 8 月 8 日我同玛·伊(即 茨维塔耶娃)一起疏散到叶拉布加。17 日抵达。26 日玛·伊 到契斯托波尔去了两天;后于 28 日返回叶拉布加,8 月 31 日自缢。她被葬在叶拉布加墓地。她给我的最后一封信在 我身边。我于 9 月 8 日去契斯托波尔,9 月 28 日转赴莫斯 科,9 月 30 日抵达。” 格奥尔吉在母亲死后保存好她的手稿。在塔什干中学 毕业,后就读于莫斯科文学院。与他同龄的孩子相比,格奥 尔吉具有很高的智商,他极富有文学艺术才华,他遗留下来 的日记、书信和素描便是明证。他于 1944 年初应征入伍开 赴前线,1944 年 7 月牺牲于白俄罗斯境内。 1.“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不值得留恋......” 茨维塔耶娃于 1922 年 5 月携幼女阿里阿德娜(阿利娅) 离开苏联出国投奔丈夫,先在柏林逗留了些时日,后在布拉 格滞留了三年,1925 年 11 月移居巴黎。在国外十七年当中, 由于生活贫困不得不数度由城市移居乡村,可以说大部分 时间都是在布拉格和巴黎近郊的村庄度过的。 书桌这组诗共 6 首,选译 3 首。据阿里阿德娜·埃夫伦回忆母亲茨维塔耶娃如何创作时说:“把所有的工作,所有的刻 不容缓的事记下来,一大早开始,趁着头脑清醒,肚子空空 的、瘪瘪的。倒上一小杯滚热的黑咖啡,放在书桌上,一生 中每一天她都怀着如同工人走到车床前一样的责任感,必 然的、不可能不这样的感情走到书桌前。此时此刻书桌上 一切多余的东西,都推到一边,以一种下意识的动作腾出一 块地方放笔记本和胳膊肘。用手掌支撑着额头,手指插到 头发里,立刻便能打坐入静。除了手稿,一切都充耳不闻, 视而不见,只见她以敏锐的思维和笔锋埋头于手稿中。” 2.“比爱情更坚贞......” 茨维塔耶娃不止一次回忆说,她从童年时代便开始写 诗,但是显然最后意识到自己的诗歌的天赋是在 1903- 1904 年,也就是十一到十二岁的时候。 “花楸果树......” 这首诗是与“乡愁啊,这早就已经......”一诗同时写的, 交相辉映。 “乡愁啊!这早就已经......” 这首诗据研究者推断,是对帕斯捷尔纳克 1928 年写的《致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一诗的唱和。又据利·楚可夫斯卡娅 回忆,茨维塔耶娃在 1941 年疏散到叶拉布加时曾为友人朗 诵过这首诗,但是由于难以抑制的内心痛苦,全诗没有朗诵 完她却戛然而止,以至于那最后的意味深长的四行诗直到 50 年代才为苏联国内所知。 报纸的读者 茨维塔耶娃在 1925 年的一封信里写道:“报界使我感到 可怕,除了使我憎恨报纸,憎恨这人的卑鄙的自发势力的一 切以外,——我为它的鬼鬼祟祟,为它的相等的字数的诡诈而憎恨它。” 给一个孤儿的诗 这组诗共 7 首,选译 2 首。组诗是献给诗人阿·施泰 格尔(1907-1944)的。茨维塔耶娃与他通信前并不认识他, 而是通过他的姐姐、女诗人阿拉·戈洛温娜认识的。1936 年 8-9 月间,她在萨瓦的一个小山村逗留时收到了患肺病 而又刚刚遭到不幸的爱情的施泰格尔的来信,信中充满绝 望的求援的“哀号”,——茨维塔耶娃立即热情地复了他的 信——每天一封,鼓励他,安慰他,寄去
关于“致一百年以后的你怎么样”这个话题的介绍,今天小编就给大家分享完了,如果对你有所帮助请保持对本站的关注!
本文来自作者[落花倾城]投稿,不代表乐毅号立场,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leheathy.com/changshi/202508-2808.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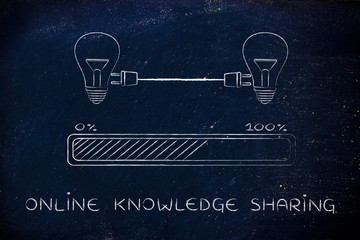



评论列表(3条)
我是乐毅号的签约作者“落花倾城”
本文概览:网上有关“致一百年以后的你怎么样”话题很是火热,小编也是针对致一百年以后的你怎么样寻找了一些与之相关的一些信息进行分析,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希望能够帮助到您。“我的...
文章不错《致一百年以后的你怎么样》内容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