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有关“历史的观念的内容简介”话题很是火热,小编也是针对历史的观念的内容简介寻找了一些与之相关的一些信息进行分析,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希望能够帮助到您。
柯林武德在导论中开明宗义提出:“本书是历史哲学的一种尝试。”“我在这里所努力做的就是对历史学的性质做一番哲学的探讨。”为此,他对历史学的四个基本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历史学的定义是:史学是一种研究或探讨:历史学的对象是人类“活动每迹”,即弄明白人类在过去的所作所为;历史学家是通过对征据的解释而进行研究的;历史学的作用是“为发”人类的自我认识,其价值就在于告诉我们人已经做过什么,人是什么。今天存在的那种历史学是4000年来形成的。那么,它是怎样发生的,经过哪几个阶段,该书第一至四编回答了这些问题。
第一编:希腊一罗马的历史编纂学。柯林武德指出,发源于地中海和美索不达米亚的近东、北非海岸地区的历史学是一种准历史学,因为这些陈述并不是对问题的答案,而仅是作者已知的东西,它所记载的不是人类的活动,而是神明的活动,因此可称之为神权历史学。准历史学的两种形式(神权历史学和神话)统治整个近东直至希腊兴起为止。
“与此相比,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的著作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新世界”。希腊史学不是传统,而是研究,不是神权主义的,而是人文主义的。“历史学”是一个希腊名词,原意只是调查和探究。希罗多德采用它作书的标题,从而标志着一场文学革命”,使希氏本人成为历史学之父。这种转变是与希腊人生活的特定条件密不可分的。但是,他们又不可能把历史学当作科学,而仅当作知识的集台,因而存在历史目光短浅、题材局限等缺陷。希罗多德风格是平易、流畅而有说服力的,而修昔底德的风格是粗硬、造作而令人反感的。因而后者不是前者史学的继承人,而是一个把前者的历史思想掩盖并窒息在反历史的动机之下的人。在希腊化时期,斯多葛派把世界作为一个单一的历史单位,则是其典型特征,它创造了普世历史观念的希腊主义。到了波里比乌斯时代,新型历史观成熟了。“他使用了历史学这个词,这是现代意义上的使用,……这是第一个主张为这门学科本身进行普遍研究的鼓吹者。”
波里比乌斯的史学思想传入罗马。李维所述的罗马史,在罗马人心目中就不是“许多种可能的特殊历史中的一种,而是普通的历史了,是唯一真正的历史现实的历史,即普遍历史”。“而作为一个历史史献的贡献者,塔西佗就是一个巨人,但他是否是个史学家值得怀疑。因为他刻画有物人损于真实。”
希睹和罗马历史编纂学的特点:一是人文主义的,是人类事迹、人的目的、人的成功与失败的历史;二是实质主义的,这是它的主要缺点。因为它建立在一种形而上学体系的基础上。
第二编:基督教的影响。柯林武德认为,公元0~5世纪是欧洲历史编纂学的第二次转折。这一时期。基督教扬弃了希腊—罗马史学的两个主导观念。基督教的历史学认为历史的过程并不是人类的目的,而上帝的目的的实践,因而历史过程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具有同样性质。“根据基督教的原理撰写的任何历史,必然是普遍的、神意的、天启的和划分时期的”。
专门致力研究这种观念的中世纪历史编纂学的“伟大任务”就是要发现和阐这种客观的或神的计划这一任务,历史学应依照上帝的启示,向人们解答上帝过去的,未来的所作所为。可见,“神意在历史中的作用得到了承认。但它却是以一种再没有任何留给人类去做的方式被承认的”。历史学家们陷入了自以为能预示未来的错误之中,“倾向于在历史本身之外去寻求历史的本质,办法就是使目光脱离人类的行为以便窥测上帝的计划”。
“中世纪结束时,欧洲思想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对历史研究进行一番崭新的定向。”“于是随着文艺复兴,人们就又回到一种基于古人看法的人文主义历史观上面来。”史学思想又一次把人放在它的画面上的中心地位。历史变成了人类激情的历史,被看作是人性的、种必的一种必然体现。这场运动的积极成果,首先见之大举清除中世纪历史编纂学中一切幻想的和毫无根据的东西。17世纪初,培根就提出“记忆主宰着历史学”,也就是说历史学的主要工作是以其具体事实追忆和记录过去。而笛卡尔根本不相信历史是知识的一个分支。他的怀疑主义导致17世纪下半叶笛卡尔派历史编纂学的出现。这个新学派是以系统的怀疑主义和彻底承认抵制原则为基础的。
笛卡尔学派的反历史倾向,恰恰导致了它的跨台。强大的反笛卡尔运动于18世纪初兴起。第一次进攻是由维科发起的。他根据Verum—factum(真理一事实)的原则,提出历史是人类社会和他们的制度的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历史在某些时期具有普遍性质,它的周期性运动并不是周而复始的一种单纯的循环,不是一个圆而是一个螺旋。“在这里,……我们第一次看到了…个完全近代的观念。”
“第二次——而且就其历史影响的所及而言,对笛卡尔主义是远为更加有效的攻击——是洛克学派所发动的攻击,它在休谟的身上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一派对哲学朝向历史学重新定向作出了贡献:一是否定天赋观念而坚持知识来自经验,二是否定了有意沟通所谓的观念和事物之间的鸿沟的任何论证,三是否定抽象观念并坚持一切观念都是具体的。
这两次进攻为启蒙运动中“人类普遍的历史”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第三编:科学历史学的滥觞。柯林武德认为,科学的产生,需要两个前提:一是历史学的视野必须放得开阔,二是人性作为某种一致的和不变的东西这一概念,必须加以抨击。浪漫主义运动之父卢梭及其后继者赫德尔提出的种族差异论认为。不同的人种所遗传下来的心理特征亦是千差万别的,不同种族的社会政治制度之间的差异正源于上述心理差别。而康德的自然规律和自然计划“二者平行论”把历史描绘成人类精神自我发展的过程。康德的两位学生席勒和费希特亦未能跳出他们的先生所设下的臼巢。
“由赫德尔于1784年所开始的历史学运动,到黑格尔而达到了高峰。……任何只读过他这部《历史哲学》本身的人,都不能不认为它是一部深刻独创性的和革命性的著作,在书中历史学第一次充分成熟地走上了哲学思想的舞台。”他提出了一种新历史学,叫做历史哲学。”但是历史哲学对他来说并不是对历史的一种哲学反思,“而是把历史本身认为一种更高的势力并使之变为哲学的而不是单纯经验的东西”。“这种哲学性的历史将是一一部人类的普遍的历史”,“而且将显示从原始时代到今天的文明的进步”。
“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并没有放弃黑格尔的这一信念:历史是有理性的.……。”他的弟子之一马克思“把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头脚倒置过来”,把“黑格尔已往宣布从自然科学的管辖之下解放出来了的历史学,又一次隶属自然科学的管辖之下”。然而“历史学的实践在十九世纪里变得愈来愈加怀疑所有的历史哲学都是些毫无根据的臆测。这一点和那个世纪之普遍倾向于实证主义有关”。实证主义认为研究自然和历史包括两件事:首先是确定事实,其次是构成规律。
在第四编:“科学历史学”中,柯林武德分别考察了英、德、法、意等国科学历史发展的概况。在英国,布莱德雷于1874年写成的《批判历史学的前提》一书,揭开了考据历史学的序幕。他的史学思想的出发点是:“实在所包括的既不是孤立的特殊,也不是抽象的一般,而是分别的事实,这些个别事实的存在乃是历史性的。”布莱德雷的思想造就了威尔逊和牛津的实在主义及罗素和剑桥的实在主义,导致19世纪晚期历史研究中普遍出现的蔑视历史哲学的倾向。
值得一提的是与上述倾向格格不入的史学家伯里。在其前期研究中遵循了“历史就是有关个体的知识”这一准则,但在后期则陷入了“历史是偶然性”的组合的泥沼。“代表着历史学思想通过从内部来对它的原则进行哲学批评而由实证主义阶段转变到理想主义的阶段。”与奥克肖特氏相对照,汤因比的《历史研究》“重申”了实证主义。汤因比认为历史的主题是人类某些单元,研究对象是各种文明。一个文明的衰落也是另一种文明的兴起,“只是历史学家个人缺乏知识或同情心。才阻碍了他看到无论任何历史过程都有这一双重特征,即它同时既是创造性的而又是破坏性的”。
在德国,“到19世纪末,人们对历史理论而特别是历史学与科学之间区别的性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此后目益增长”。著名的哲学史家义德尔班认为,“科学以总结普遍规律为其目的,而历史则以描述个别事实为其目的”。这样,历史学就以全盘被驱逐出知识的领域而告结束。哲学家齐美尔看到,自然的事实与历史的事实并不是同一意义的事实,后者不能被感知或实验,“历史学家面前所有的一切只是文献和遗迹,他必须想方设法从其中重新构造出事实来”,“历史是一种精神的东西,是一种人的个性的东西……” 可见,齐美尔没有完全摆脱实证主义的影响
20世纪初。近代德国杰出的史学家迈耶在他的论文《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论》中,彻底地批评实证主义的倾向,“把历史设想为一种从外部所看到的纯粹景象,而不是一种过程,——即历史学家本人既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又是对它的自我意识。历史学家与他的题材之间的密切无间的全部关系就消失了,历史重要性的概念就变得没有意义了”。因此,柯林武德一针见血地指出:“迈耶的有赖于选择重要事件的历吏学方法的原则,也就消逝于一缕轻烟”。
可以说。“法国这个实证主义的发源地也是实证主义受到最坚强和最出色的批制的国家”。现代法国哲学家拉希利埃的中心思想是知识本身就是自由的一种功能这一观念,“而柏格森对意识的分析就为历史理论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贡献”,近代法国历史编纂学沿着他的著名法则,“立足于运动”而前进,于利昂的《高卢史》、艾利·阿累维的《英国人民史》便是明证。
就意大利而言,19世纪涌现出以罗齐为代表的杰出史学家。1893年他27岁就写出使他一举成稆的论文《纳入艺术慨念之下的历史学》,从根本上否定了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在他心目中,“真正的历史对纯属或然的、或者纯属可能的东西是不留余地的;它允许历史学家所肯定的,就只是他面前的证据所责成他去肯定的东西”。
第五编“后论”实质上是柯林武德本人的历史观的反映。在这里,柯林武德对历史学的本质、历史学的基本特征、历史学的社会作用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因而这篇“后论”是把握作者思想的关键。
作者坚持这一论题,“研究自然的正确道路是靠那些叫做科学的方法,而研究心灵的正确道路则要靠历史学的方法……。历史学就是人性科学所自命的东西”。因而,一切人类的行动都是历史学的题材,当然历史学家并不关心人们的吃、睡等自然过程,而关注人们的思想及其创造过程。从这个角度说,历史学是“作为心灵的知识”。另一方面,历史学既不同于科学也不同于抽象,而是将二者结合起来的“第三种东西”,它最本质的东西是记忆和权威,由此构成”一种想象的网”。这张“网”的特征是:(1)它必须在空间和时间;(2)一切历史都必须与它自己相一致;(3)历史学家的“图画”与叫做证据的某种东西处于一种特殊的关系之中。
那么,这种历史的证据有哪些,柯林武德罗列了推论(包括演绎和归纳两种)、证词、“剪刀加浆糊”等类型。并指出,依赖上述证据的历史学都不是真正的、科学的历史学。历史学的真谛是:“历史学家必须在他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因而。“只有能够在历史学家的心灵里加以重演的东西才是历史知识”。它包括两点,一是经验,二是思想。离开了这两点,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有历史。这就决定了历史思维的特征是反思。历史研究的终极目的是获得自我认识,求得人类的进步。
“一切历史归根到底都是当代史”怎么理解
如果说克罗齐以精神的绝对本质来展开历史的哲学批判,建立起自己的历史学体系,那么柯林武德则以思想的行为原则来解释历史哲学,开辟了新的历史认识道路,柯林武德批判的历史哲学的目的是要确立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自主性,而且以其毕生精力致力于历史学与哲学之间的沟通。
为此他认为:
1.行动是达到事件外部与内部统一的基础:他指出,研究过去某一事件的历史学家,总是把可以称之为事件的外部方面和内部方面加以区别,所谓事件的外部方面是指可以用物体及其运动来描述的一切事物,如恺撒领兵在某个时刻渡过了卢比孔河,事件的内部方面是指只能用思想来描述的内容,如恺撒对共和国法律的蔑视,或他本人和他的谋杀者之间有关宪法政策的冲突,历史学家不能只注意一方面而必须兼顾双方。
所探讨的不是单纯的事件而是行动,行动是一事件的外部方面和内部方面的统一。
历史学家的“工作可以由发现一个事件的外部而开始,但他决不能在那里结束,他必须牢记事件就是行动,而他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把自己放到这个行动中去思想。”
2.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从上述观点出发,柯林武德很自然地区别了自然科学和历史学,他认为自然界的事件就是单纯的事件,自然科学家的工作就是观察这些事件彼此之间的联系,从而把它们纳人一般的公式或自然规律。
历史学则不然,历史的过程不是单纯事件的过程而是行动的过程,它有一个由思想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而历史学家所探讨的正是这些思想过程,所以,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历史研究的任务就是要发现隐藏森历中享宋后而的那些思想,这就需要研究者设身处地的对以往的思想进行再思考。
3.关于“思想重演”:柯林武德强调今日史学家的思想必须进人昨日古人的思想中去,彼此产生心灵的沟通,使自己重演过去的历史,然后才能解释古人思想的表现,即具体的历史过程,历史学家的任务是从推理上研究那些无法直接观察到的事件,而对之研究必须建立在观察所及并感到兴趣的事物—“证据”之上。
但引证权威的证据而加以组合起来的不是历史,这种剪刀加浆糊的历史之所以不成其为历史,是因为它过于迷信权威,缺乏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所应有的自主性和批判精神,真正的历史学家必须具备构造历史的能力,就是“历史的想象力”。
不可否认,历史活动者的许多行为在许多方面超出了历史学家的活动能力,因而也就超出了它的重现能力,这种过高的要求难免使有些历史学家只能是心之向往,力所难及。
推荐一两本关于历史的书。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诠释
--读《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有感
1、 基本说明
对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柯林武德曾这样评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并非在这个词的通常意义上,即当代史意味着为期较近的过去的历史,而是在严格的意义上,即人们实际上完成某种活动时对自己的活动的意识。
因此,历史就是活着的心灵的自我认识” 。
这段话恰当的说明了这一命题的重要内涵——当代史是自我认识在历史中的再现。
而要把这种再现归结为历史本身,重心就自然而然地落在了当代史对历史的全面涵盖,这种涵盖需要对当代史做出一番新的诠释:“‘当代’一词只能指那种紧跟着某一正在被做出的活动而出现的、作为对那一活动的意识的历史” 。
当代并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更多的是一个思想概念。
正如克罗齐自己所表明的,“当代”是对历史做出叙述时所出现的一种思考状态。
这种思考无疑是思想的现实化和历史化,并通过思想的历史花进而发现了历史学的真谛所在,即: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在这里,作为主词的历史与作为宾词的当代史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当代之所以能够穿透死亡的束缚而规定了历史的全部内涵,原因在于外在时间和编年史意义上的年代序列派生了历史思维的内在时间 ,这种与思维具有同一性的内在时间通过生活和实际行动达到了哲学和历史的合一,或者说是思想与历史的合一。
“历史决不是关于死亡的历史,而是关于生活的历史” 。
在克罗齐那里,历史重新复活了,而且是以生活的名义、并借助思想的当下性成为正当的历史。
然而,这种“关于生活的”当代史却很容易受到恶意的曲解和善意的误读,特别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成为人人皆知的口号之后,误解就更深了:似乎当代史的历史就意味着历史学家对于历史拥有绝对的权利,而不管这一权利的出生证明是什么;如果历史仅仅是当代史,历史学家似乎还可以根据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书写历史,因为这也是当代史,而且是绝对肯定的历史。
相反的错误观念也存在,富有历史正义感的历史学家可能会想当然的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明显存在着对历史事实的猥亵,这是决不能容忍的轻率行为;退一步讲,即使当代史对历史事实的误解只是一个小错误,那么,当代史的提法也是缺乏历史感的,因为根据显而易见的字面阐释,如果历史只是当代史,那么还有什么历史进步、历史动因可谈?
对于上述诸种错误之看法,笔者是试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2、 历史叙述的权利
确实,当历史学家以思想的名义进行历史叙述时,历史学家是自由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没有权利对历史学家提出自己的要求。
“毫无疑问,想象力对于历史家是必不可少的:空洞的判断、空洞的叙述、缺乏自觉或想象的概念,全是无用的;……,我们要求对我们所将叙述其历史的事件应有生动的体验,意思也就是要使事件作为直觉与想象重新被提炼出来。
没有这种想象性的重建或综合是无法去写历史或读历史或理解历史的” 。
简单的说,丰富的想象力是历史学家必须具备的品质,但仅仅有想象力还不够,还需要一种直觉,历史是“对个别事物的认识”,而且是对真实的历史的认识,“直觉的成分和逻辑的成分共同构成了历史判断。
在历史研究中,自觉能力的高下就成其为历史学家历史认识能力高下的一个重要尺度” 。
克罗齐之所以把编年史看作“假历史”,就在于编年史缺乏历史家的想象力和直觉对历史的当下构造,简言之,就缺乏了“当代”的、或者说是思想的在场。
想象力和直觉共同构成了历史写作的技术基础,但这种基础却不能保证想象力和自觉的恰当运用。
如果历史学家凭空想象某种能够证明自己某种“主张”的乌有之物,或者让“我们的爱情、眼泪、蔑视”等等克罗齐称之为“情操价值”的价值左右对历史的思考,那么,历史也不是真历史,历史也就成为一种“诗歌性历史” 。
比如对异教徒、对犹太人或者对某某阶级的仇恨融入在历史叙述当中,历史的价值就不是思想的价值了,这样的历史也不能称为历史了。
要写一部真正的历史,“我们就要清除神话和偶像,清楚朋友和情人,一心注意历史问题,那就是精神或价值(如果爱用哲学味较少而较通俗的词说就是文化、文明、进步),我们就要用两只眼睛和单一的思想目光看待它们” 。
历史的主观性不是个人情感的主观性,而仅仅是思想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不是为了张扬历史学家的爱恨情仇,而是为了实现思想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也就是历史的内在的一致性。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引人注目的另外一个误解是,既然历史是当代史,那么历史学家就有权利根据现实的需要进行历史写作。
而所谓的现实需要,可以是政治的,比如爱国主义;也可以是个人目的,比如为了说服别人而专门引用某些有利于自己的观点,而有意无意忽略了那些也曾是事实的历史事实。
克罗齐把这两种历史分别称之为“实用性历史”和“修辞学的历史”。
“实用性历史(但它并不是历史)作为一种实际活动是不受非难的:我们每个人都不仅想要探讨历史,而且想要探讨行动,在行动中很好的利用这一形象或者那一形象的重新召来去推动自己的或(结果是一样的)别人的工作。
”当代史的提法决不是为了当前的目的,或者是为了历史学家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理想而任意切割的当代史,实用性历史作为一种对历史学(注意,不是历史本身)成果的一种生活化运用而受到作者的肯定(修辞性历史也是如此)。
这并不在于这种历史所抱有的历史叙述目的具备历史学上的价值,而在于它的行动本身符合了历史的真义,这个真义就是历史是关于“生活的历史”,正如历史学家通过自己的思想来理解历史那样,实用性历史只是,而且也仅仅是作为一个当下的眼光看待历史时,它的实用性获得克罗齐的肯定,除此之外,实用性历史并无可取之处。
同样,“修辞学的历史”也“具有一定的重要性”,“我们无法攻击它而只能攻击它的理论”,这种理论就是“把历史看成是演说家的作品、……、或看成是心灵的教育(如果它是政治性的)、或看成是能引起愉快的”。
这些都表明:“修辞性历史是以一种既存的历史为前提,至少要以一种诗歌性历史为前提,是抱着一种实际目的叙述出来的” 。
这些实际目的主要是一种教化的目的,然而,“‘历史’就不仅会在一种形式之下而会在所有这些形式之下参与教育的过程。
但就历史本身而论,它只会在一种形式之下参与教育的过程,那不是纯然抽象的道德教育的形式,而是思想教育或发展的形式” 。
因此,把历史冠之以道德教育等等名义来进行思考,那还没有洞见历史,因为所这些功能或者目的,都是外在于历史的,比如为了爱国主义教育、比如为了证明某种天堂必然来临等等理想和预言。
真正的历史,是内在的、是通过思想的发展而自然达到这些思想的价值和目的。
这种思想的发展正如历史的发展,决不含有任何外在于思想的目的和价值。
那种把当代史视为一种可以供历史学家任意 *** 和曲解的庸俗看法,实际上是侮辱了克罗齐的思想(或者哲学)的真正内涵。
把历史看成是个人情感的发泄场所、或者把历史看成是一个实用的教育工具或者是政治家的政治手段,都是对“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亵渎。
3、 历史的真实性问题
历史是真实的吗?一切对当代史提出质疑的看法都或多或少认为:如果历史就是当代史,历史的真实性就无法保证。
虽然克罗齐反对以当下的任何实用性目的对历史进行“剪刀加浆糊”(柯林武德语)式的研究,但当代史本身就意味着历史的客观性无法保证。
对于历史的真实性问题,克罗齐先从不可知论的观点入手进行剖析。
不可知论“并不绝对否认历史的真实性,但它否认历史具有完全的真实性” 。
不可知论认为历史不可能是完全真实的,至少历史的全部真相不能完全被历史学家所掌握,换句话说,不可知论否认历史具备真知识。
不可知论以历史不可能达到完全的真实性而否认历史的真理性品格,但是,如果不可知论面对历史所提出的无数个历史真相问题都得到解决,“如果全部疑问都得到满意的答复,如果我们掌握了所有的答复,我们又该怎么办呢?通向无限的道路跟通向地狱的道路一样宽广,如果它不导向地狱,它就必然会导向疯人院” 。
企图解决所有历史问题的奢望是不必要的,而由于解决不了这些无穷无尽的问题而产生苦恼和失望是幼稚的,所以“即使无限的历史之全部特定的无限事物能给我们的欲望以满足,我们所该做的也只有从我们的心中把它们清除出去,忘掉它们,而只聚精会神于与一个问题相适应和构成活生生的积极历史、既当代史的某一点上” 。
历史的真理品格不在于洞察真相本身,而在于思想本身。
历史真实与否,并不是问题的核心。
克罗齐把历史的客观性问题搁置起来,这个疑问也离开了克罗齐的视域范围。
既然历史的真实性不是核心所在,那么,克罗齐又是如何对待历史叙述中必然遇到的史料问题呢?克罗齐对于史料并不怀有在一般历史学家那里常见的尊重感,他曾这样评价史料学工作者:“可怜的学者、档案工作者和考古学家是无害的,是一些有用的小人物” 。
不仅这些史料工作者是小人物,而且对于史料本身,他也认为“把想象的、虽则是以猜想形式想象出来的细节添到实在的材料上去也是可以被容许的” 。
当然,这种想象性不是“要求历史把他们带回到中世纪的古老堡邸和市场中去”,而是“在想象中去重现过去,并从现在去重想过去,不是使自己脱离现在,回到已死的过去” 。
克罗齐很诚实的道出了那些标榜以真实性为第一要义的历史学家所特有的虚伪性。
既然历史的真实性是不能实现的一种理想境界,那么,历史学家的文学想象能力也是可以容许的,如此,历史学家何必要遮遮掩掩自己并不孱弱的想象力?当然,克罗齐对史料的漠不关心并不是对历史的无知,恰恰相反,这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内在逻辑使然。
“以证据为依据的历史归根到底完全是一种外在的历史而决不是根本的、真正的历史,根本的、真正的历史是当代的和当前的” 。
用证据来说明历史,而不是用思想来理解历史,历史就退化为编年体历史了,其中全无血肉和心灵,更无人类的意识,而只有死亡的过去。
“任何过去有过的事情都不会返回,任何过去有过的事情都不能被取消;即使我们恢复了一种古老的思想,新的敌手也会使保卫变成新的,并使思想变成新的。
”尽管克罗齐对于死亡的过于怀有一种体面的尊重,但历史的核心决不在于过去,而在于现在。
苛求历史学具备完全的历史真实性无疑是苛求历史学对过去的全知全能,这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因为历史学的真正主题是当下的时代精神或个人心灵所指引的历史。
4、 哲学与历史的合一
思想本身是不断演进的,历史真实的记录了人类意识的演进,而且历史也从思想、或者哲学中得到了规定性内容。
“精神就是世界,它是一种发展的精神,因而它既是单一的,又是分歧的,是一个永恒的解决,又是一个永恒的问题;精神的自我意识就是哲学,哲学是它的历史,或者说,历史就是它的哲学,二者在本质上是同一的;意识和自我意识是同一的,也就是说,意识和自我意识既有差别,同时又是同一的,就像生活和思想一样” 。
在这样一种情境下,当代史有没有极具历史意识的“发展”可言?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不能被看成是一种没有发展观、也没有历史感的历史命题。
在克罗齐的眼中,历史和思想的内在性表明了历史的进步观念。
正如思想的不断地辩证前行,历史也是如此。
克罗齐坚持一种十九世纪以来的发展观念,这种观念坚信人类是不断前进的。
在谈及黑暗的中世纪的史学时,他也认为中世纪也是有进步的 ,不仅如此,“甚至荒谬的人的毁谤和对人类良知得令人厌恶的错误批判的毁谤也是一种前进” 。
历史是不断前行的,这点毫无疑问,也合乎逻辑的包含在“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中,那么,这种前行有没有动力,它有没有一个预先设定好的目的因?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先从克罗齐认为历史必须具备的三点历史意识谈起,“这三点是,历史事件的完整性、叙述与文献的统一性和发展的内在性” 。
如果历史和哲学互相分离,历史事件的完整性也没有实现;文献不与叙述历史、亦即思考历史的思想相统一,历史也不是历史;而发展的内在性则表明我们不能从历史之外寻找历史的发展。
在历史与哲学(或思想)相分离的情况下,历史学家只承认历史的动因只能从事实本身去寻找,先搜集历史,然后再从事实中寻找原因。
这看上去很公正可靠,但这种被克罗奇称之为“实证主义”的做法却直接把各种庸俗的、陈旧的观念放逐于批判领域之外,他们“求助于求学时的记忆,求助于当时流行的哲学口号,求助于当时人们对于政治、艺术、道德的日常情操” ,并让这些观念毫无顾忌的引导历史学家编造一个关于历史原因的平庸传说。
这看似尊重历史,实质上各种偏见、误解的大杂烩。
而那种以非历史的哲学思想与历史结合时,情况更为糟糕。
比如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比如某种客观规律,他们博学而又自信的认为,历史有一个最高的终极原因,而且存在一个终极的目的,这种目的是外在于历史,比如天堂,比如共产主义社会。
他们依据自己的需要,对历史进行人为的切割以至歪曲,然后采用这些所谓的历史事实比附他们的观念。
这种做法与证明世上存在上帝的那些常用手法是没有多少差别的,他们既玷污了哲学的名誉,又使历史只能充当类似注脚的角色,甚至“把单纯的叙述性的历史当作身外的废物,而单纯叙述性的历史则应当作为道德家和政治家说教和教训的原料或脚本” 。
如果事实果真如此,历史就可以完全取消,而单纯的奇思妙想就可以代替历史叙述了。
这样思考出来的终极原因决不是历史的动因,同样,所谓的历史必然趋势也不是历史所渴求的天堂。
从上面可以看出,克罗齐既否认单纯从事实本身寻找历史发展原因的方法,也反对以观念的逻辑代替、说明历史的逻辑。
如此,克罗奇所认为的历史动因又是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从克罗齐所定义的“哲学”一词谈起。
克罗齐认为,真正的哲学,“只能是史学的方法论阶段,即,关于构成历史判断的范畴的阐述或关于指导历史解释的概念的阐述” 。
没有任何哲学能够离开历史的基础,“一般研究历史事项的人都应当成为自觉的和有训练的哲学家,因而一般的哲学家,即纯哲学家在知识的专业化中应当是无立足之地的” 。
从这个定义中,我们至少可以明白以下几层含义:一是哲学给予历史以叙述的意义,没有哲学,历史就不成为历史了;二是历史给予哲学实在的存在理由,如果离开了历史,哲学就不能叫哲学。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历史发展的动因问题——如果对于克罗齐而言可以构成一个合法提问的话——不能从历史之外的纯哲学当中寻找,当然也不能单纯中历史事实中寻找,而应当克罗奇的历史化哲学和哲学化历史、亦即思想中去寻求。
正如克罗齐自己所说的,“思想从内部重整历史,它就是它自己的证据,它不承认不可思议的东西,因为那是不能想象的” 。
5、 结语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恰当的表明了克罗齐的史学思想,但我们决不能忽视它的内涵及其背后的观念预设,更不能把这一命题口号化。
许多错误的理解都是从一知半解中产生的,如果我们不能从克罗奇的整体思想本身去理解这一命题,那当代史这一命题就无任何价值了,更谈不上后人还能从中获得什么新的启发,思想的进步也会由此停止,正如克罗齐所说,“当人们认为已经不能再学习时,当人们被教育成再没有接受更好教育的可能性时,生命就停止,再不能说还活着而应说已死亡” 。
枪炮、病菌与钢铁
--------人类社会的命运
美 贾雷德 。戴蒙德
中国政法大学杨玉圣老师开的书单:
题记:这是一份企图供非历史学专业的大学生和其他历史爱好者参考的历史学名著推荐阅读书目。本书目涵盖古今中外,以名家名著为主要选择取向,特别是兼顾其学术权威性、阅读美感性和不可替代性等方面,希望能有助于人们对历史学的基本了解与理解,推进读书与思想风尚,并努力把握历史的原脉、现况与可能的未来走向,关心祖国的未来与人类的命运。
一、概论
01《历史是什么》,爱德华?H.卡尔著,吴柱存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02《历史的观念》,柯林武德著,何兆武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03《历史学家的技艺》,马克?布洛赫著,张和声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二、中国史
03《史记》,司马迁撰,中华书局版。
04《资治通鉴》,司马光撰,中华书局版。
05《国史大纲》,钱穆著,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06《观堂集林》,王国维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07《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苏秉琦著,三联书店1999年版。
08《东晋门阀政治》,田余庆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09《万历十五年》,黄仁宇著,中华书局1982年版。
10《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孔飞力著,陈兼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11《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官僚政治之经济的历史的解释》,王亚南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12《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李伯重著,三联书店2003年版。
13《剑桥中国晚清史》,费正清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14《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陈旭麓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5《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茅海建著,三联书店1995年版。
16《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著,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三、世界史
17《伯罗奔尼萨战争史》,修昔底德著,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
18《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雅各布?布克哈特著,何新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19《西方世界的兴起》,道格拉斯?诺斯著,厉以平等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
20《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巴林顿?摩尔著,拓夫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21《论美国的民主》,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22《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版),罗荣渠著,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23《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斯塔夫里亚诺斯著,迟越等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四、人物传记
25《孔子评传》,匡亚明著,齐鲁书社1985年版。
26《柳如是别传》,陈寅恪著,三联书店2001年版。
27《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注译,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8《富兰克林自传》,姚善友译,三联书店1985年版。
五、历史地图集
29《中国历史地图集》,谭其骧主编,中国地图出版社 1982-1988年版。
30《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主编(中文版编辑:邓蜀生),毛昭晰等译,三联书店1985年版。
关于“历史的观念的内容简介”这个话题的介绍,今天小编就给大家分享完了,如果对你有所帮助请保持对本站的关注!
本文来自作者[遇文轩]投稿,不代表乐毅号立场,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leheathy.com/zlan/202508-4462.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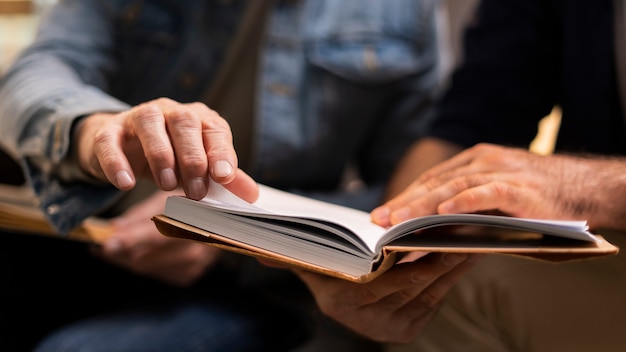





评论列表(3条)
我是乐毅号的签约作者“遇文轩”
本文概览:网上有关“历史的观念的内容简介”话题很是火热,小编也是针对历史的观念的内容简介寻找了一些与之相关的一些信息进行分析,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希望能够帮助到您。柯林武德在...
文章不错《历史的观念的内容简介》内容很有帮助